1930年6月17日,面對全球一片反對聲,美國第31任總統赫伯特·C.胡佛依然執意簽署了《斯姆特-霍利關稅法案(Smoot-Hawley bill)》,將2萬多種進口商品的關稅提升到史無前例的高度。
時任胡佛總統顧問的J.P.摩根首席執行官托馬斯·W·拉蒙特后來回憶說,那一天,他幾乎要跪下來懇求胡佛總統懸崖勒馬,別讓這項愚蠢至極的法案成為現實。但胡佛沒有聽,“他甚至可能根本沒有意識到,自己正在打開的是一個吞噬全球經濟的潘多拉魔盒”。
從那一刻起,美國挑起的全球關稅大戰全面升級,國際貿易體系四分五裂,經濟鏈條斷裂崩潰。在美國國內,工廠倒閉,銀行破產,失業潮席卷全國。法案通過當年,美國失業率為7.8%;到1931年,驟升至16.3%;1932年達到24.9%;1933年達到25.1%。
此舉給當時已經非常脆弱的國際經濟體系一記重擊:許多國家對美國采取了報復性關稅措施。1930年,美國對英國的出口有70%是免稅的;到1931年底,這一數字下降到20%。從1929年到1932年,美國的進出口總額銳減近70%;其中出口下降了49%,進口下降了40%。在1929年到1933年間,全球貿易總額下降了26%。直到20世紀30年代末,國際貿易都沒有恢復到1929年的水平。
當代大多數經濟學家都認為,大蕭條之所以程度如此之深、時間如此之長,很大程度上是因為《斯姆特-霍利關稅法案》將美國國內的經濟困局推向全世界,而國際經貿局勢由此產生的負面影響又反向回流到美國,最終導致全球性經濟金融危機。
另有一些經濟學家認為,雖然該法案是在1930年通過的,但關于該法案的討論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,事實上早已引起資本市場強烈不安。從某種程度上來說,這也是導致1929年10月美國股市大崩盤,進而拉開大蕭條序幕的重要“推手”之一。
美國前副國務卿、世界銀行前行長羅伯特·佐利克的新作《論美國:美國外交及外交政策史》中文版中,也對這一段歷史作了詳細記述。
佐利克援引歷史資料稱,大概有65個國家對當時的新關稅法案表達了抗議,但“國會從來沒有認真考慮過國外對法案的反應”。比如,查閱《國會議事錄》長達20頁的“關于西紅柿關稅的辯論記錄”可以發現,“里面幾乎沒有人提到過國會這樣做將帶來什么樣的國際影響”。作者吐槽道:“美國在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里,都在收拾1930年的貿易法案給國際貿易留下的爛攤子。”
佐利克多次強調自己是“自由貿易的支持者”,并表示“我堅信自由貿易是一件好事。實施關稅壁壘將推高成本、降低生產率,并增加經濟系統運行的阻力”。他還明確表達了自己對當前美國關稅和貿易政策的擔憂:“在我看來,美國的優勢曾在于其開放性,不僅對商品,也對資本、思想和人才開放。”
佐利克的外交生涯貫穿了世紀之交的30年,他歷經里根和布什父子三任總統,是后冷戰時代共和黨內最核心的幕僚之一。可能正是基于在經貿、金融和外交領域多年的工作經驗,相較于其他外交家,他更關注貿易政策與外交戰略的關系。在他看來,關稅與貿易政策并不僅僅是美國外交戰略的“一個組成部分”,而是“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”,尤其是對于美國這樣一個以貿易為立國之本的國家而言。
關稅與美國政策走向自美國建政之初就糾纏不清。美國獨立戰爭的導火索波士頓傾茶事件,就與關稅政策變動密切相關。當今的關稅政策又成為美國外交政策中的焦點。“美國人不僅將其視為一種獲取經濟收益的形式,更相信隨著貿易新規則的確立,國際體系也會隨之改變。”佐利克認為,從大蕭條時期的貿易保護主義到冷戰時期的技術出口管制,經貿在美國外交中始終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。
佐利克在書中援引達特茅斯學院經濟學教授道格拉斯·歐文(Douglas Irwin)的觀點,將美國貿易政策分為3個階段,每一個階段都以當時國會的首要目標為標志,分別為“收入”“限制”和“互惠”。
在“收入”階段,美國幾乎完全依靠關稅收入為新政府提供資金,并以此支付美國獨立戰爭(1775年至1783年)期間欠下的巨額貸款利息。在此期間,美國開國元勛之一、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·漢密爾頓提出了包括保護關稅、出口限制、對于目標產業的直接政府補貼、對于制造業投入的稅收減免、提供公共設施等基本政策原則,這也為以后的保護主義政策的發展設計出主要政策框架。
南北戰爭(1861年至1865年)開啟了下一個階段,也就是限制性的貿易政策階段。此時,北方急需收入以支撐戰爭開支,為此國會將進口商品的平均關稅提高到了約50%。這一稅率水平基本維持到了19世紀結束。
到19世紀末、20世紀初,全球經濟整體處于調整階段,美國國內貿易局勢也在發生變化。傳統上,美國農民,特別是種植棉花和谷物的農民以及一些畜牧業從業者,都是出口的“重度依賴者”。后來,美國的大制造業主也成了凈出口的一方,他們都倡導進一步調降關稅,以支持出口。但是,大多數小制造業主并不同意他們的觀點。
在很長時間里,爭論的雙方都沒能獲得太明顯的優勢。直到一位當時非常有名的調查記者艾達·塔貝爾發文聲討物價上漲,稱“關稅是腐敗政客和特殊利益者碗里的肥肉”“抬高了勞工家庭的生活成本”,輿論開始偏向自由貿易。
美國第28任總統伍德羅·威爾遜也聽到了這些呼聲。1913年,《安德伍德-西蒙斯關稅法(Underwood-Simmons bill)》頒布,將進口商品的平均關稅從40%削減到27%,并將許多商品加入免稅品清單。
然而,此輪調降關稅的政策沒能延續太長時間。
1920年,美聯儲緊縮銀根,引發了嚴重的通貨緊縮和經濟滑坡。佐利克吐槽道,美國國會對此的反應是“又一次祭出了他們最熟悉的救急方案”——提高關稅。
不過,在他看來,此次提高關稅更大的影響是,為日后美國政府的操作留下了一個重要的“口子”:當時,國會與國務卿查爾斯·埃文斯·休斯合作,通過了一個較為靈活的關稅條款,試圖允許總統根據專家對“生產成本的計算”來調整稅率。“雖然這項政策后來被證明缺乏可行性,但它創造了一個重要的先例,使國會可以把調整關稅的權力授予行政機構。”這一授權后來于1928年獲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。
緊接著,就輪到被后人斥為“最愚蠢法案”的《斯姆特-霍利關稅法案》出場,并在整整4年后的1934年6月被扔進了“歷史的垃圾堆”里。
很多專家認為,于1933年開啟第一個任期的美國第32任總統富蘭克林·羅斯福在美國貿易史上的地位被嚴重低估了。佐利克雖然沒有對這一評價給出正面回應,但他在書中著重描繪了一個細節:
1934年2月28日,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召集副總統、國務卿、參眾兩院中的民主黨領袖、農業部部長和另外幾個人,一起商議新草案。新草案的提議“很大膽也很簡單”,即向行政機構授權,使其可以通過貿易談判把《斯姆特-霍利關稅法案》規定的進口關稅下調或上調最多50%。這個草案隱含的前提是“國會對總統的授權”,這就讓行政班子繞過了參議院的職能。此外,國會僅需投票一次,因為這項新權力是沒有時間限制的,總統可以通過這項法令獲得極大的權限。
1934年,《互惠貿易協定法》得以通過。“這一次革新對美國貿易政策的改變是巨大的。此后美國大多數總統可以參考這個先例來制定貿易政策,也即把外交政策和經濟政策的目標結合在一起。”佐利克認為,此后很長一段時間內,美國貿易政策的重點從“把關稅設定得越來越高”變成“通過協議來減少壁壘”。至此,美國貿易政策也進入了第三階段——“互惠”。
以上便是佐利克結合自身與多位專家的觀點,重新梳理出的美國關稅與貿易政策的脈絡。他直言不諱地評價其“看起來左搖右擺”,其實不過只是“對當時形勢的一種實用主義回應”。
縱觀美國貿易政策乃至整個外交戰略可以看到,美國常常在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、孤立主義和“世界主義”、貿易保護主義和自由貿易之間搖擺,“但它之所以能夠搖擺,離不開那條實用主義的繩索”。(作者:韓 敘 來源:經濟日報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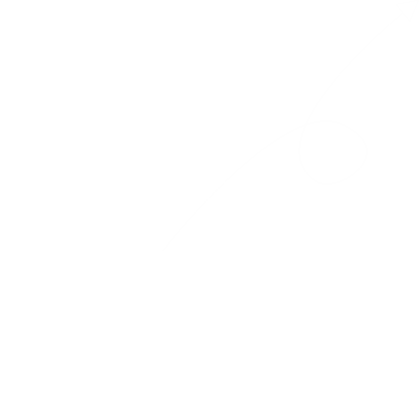
 手機看中經
手機看中經 經濟日報微信
經濟日報微信 中經網微信
中經網微信






 版权所有
版权所有 